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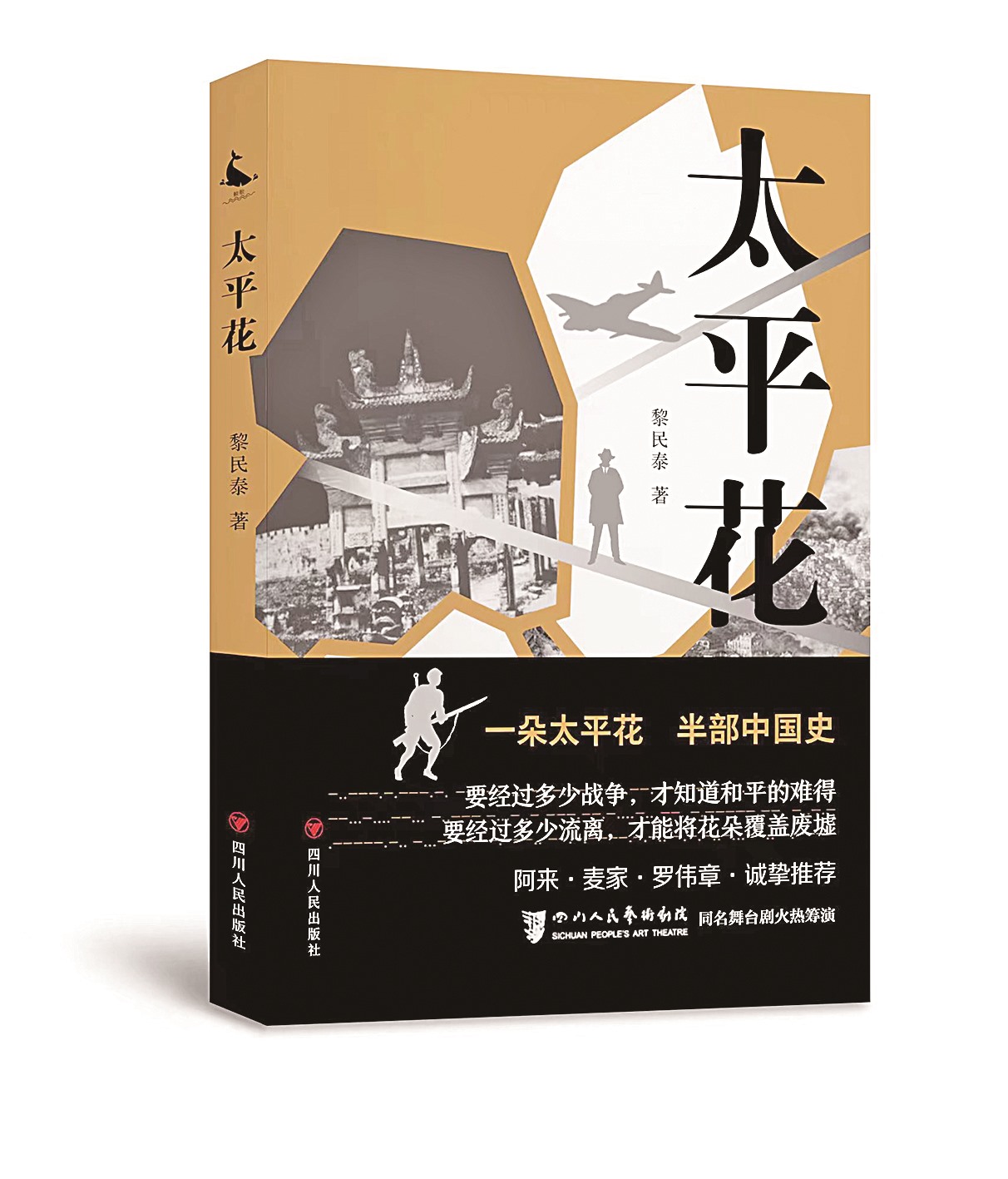
一
太平花,初名丰瑞花,早在唐代即为蜀中珍品名卉,尤以剑南道青城山中“宝仙”“醉太平”“玉真”诸品种为胜。五代后蜀主孟昶,为讨爱妃花蕊夫人欢心,下令在成都“尽种芙蓉”,“四十里如锦绣”。此间,也将青城山中的丰瑞花移往成都种植,夏初开花,繁密似雪,与秋季姹紫嫣红的芙蓉花隔季相映,成为妙景。北宋初年,程蕴之任成都知府,见此花冰清玉洁、高雅脱俗,遂“绘图以奏”,被宋仁宗赐名为“太平瑞圣花”,并移植至汴梁,名震京城,在宋祁、陆游、范成大等宋人的诗文词章里,多有吟咏。后,金灭北宋,太平瑞圣花被劫至金中都(今北京)。金灭,皇城里的太平瑞圣花被毁,只有京郊少许躲过劫难,保留下来。元、明两代,太平瑞圣花被移入紫禁城御花园内。清初,又移植到畅春园和圆明园。清中叶,嘉庆帝崩,谥号仁宗睿皇帝,因“睿”与“瑞”同音,为避讳,继位的道光帝下令将“瑞圣”二字去掉,只称“太平花”,沿用至今。然,1860年,英法联军攻入北京,毁三山五园,畅春园、圆明园里的太平花尽皆被毁,只余长春园两株幸存。几年后,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,将幸存的两丛太平花移到排云门前。不料1900年,八国联军侵占北京,太平花再遭劫难,只余一株幸存,尤显珍贵,慈禧太后常以此花赏赐王公大臣,京城权贵皆以种植此花为荣。这时,远在河南的开封(北宋汴梁)、四川的成都和青城山,名声远播的太平花,却销声匿迹,踪影难寻。直至2017年,青城山下的都江堰市,才设法与故宫联系,将一株枝繁叶茂的太平花迎归故里,种植在离堆公园内。
这就是太平花的真实故事:两次赐名,六次迁徙,纵越大半个中国,又与唐宋以后上千年的中国历史紧密关联,很精彩,也很离奇。故在迎归仪式上,有专家一语道破:一朵太平花,半部中国史!
我也亲历了那次隆重的迎归,当时就在座谈会上昂扬表态:一定要以太平花为名,写部小说!话说出去了,我才发现,究其题材,太平花当属地方性质。而地方性题材的写作,极易落入窠臼:照搬故事,敷衍成篇,很难在文学空间里腾挪。同时我也知道,历史上或生活中的故事再精彩、再离奇,也难以成为小说。小说需要更多的东西。写小说,是用一根针去挖一口井,需要作者从细小处出发,穿透故事的外壳,去发现更深的蕴涵、更广阔的世界。
此后,我便开始对“太平花”进行苦苦的“探究”与“穿透”。
二
由太平花的命名,我想到了生活中一些熟悉的事。比如青城山下有座小山,叫太平山,山下有个小镇,叫太平场。都江堰城里,原有一条街,也叫太平街。我上网搜索了一下,更是在全国各地,发现了很多与“太平”相关的地名。由此,我又想到了唐朝的太平公主、宋代的《太平广记》、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,等等。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:中国人,为什么从古至今,都喜欢用“太平”二字来描人状物,且将和平静好的岁月叫做“太平天下”,将繁荣兴旺的时代称为“太平盛世”?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性里,早就深植着“太平”因子?早就充盈着对和平的强烈向往与渴望?太平天下、太平盛世,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古来有之的人文观念和社会理想?答案是肯定的。但我在回观中国历史、回观世界历史时,却发现了一个问题:自从原始社会解体,有了私有制,有了部落、城邦和国家等权力意识形态后,人类就在不断地频繁地进行战争,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,还出现了一个专门以“战”命名的时代:战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类的历史,就是战争的历史。于是,一连串的问题随之出现:人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战争?战争的根源在哪里?战争的本质是什么?战争与和平又有着怎样的哲学关系?在思考这些问题时,我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奇怪的现象:中国自古以来出了很多兵法家,产生了许多兵法著作,但所有的兵书,都在讲如何布阵、如何施计、如何杀敌、如何取胜,就是没有一部兵书,讲人类应该如何避免战争、如何追求并享有和平。德国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我也看了,它同样在讲如何利用各种条件、调动各种因素,以确保己方在战争中获胜。我还在网上搜看了古今中外一些著名战役,比如巨鹿之战、昆阳之战、官渡大战、赤壁之战、十字军东征、滑铁卢战役、英法百年战争,以及后来的一战、二战,我发现,尽管战争爆发的原因各不相同,但归根结底,都与人类的欲望有关,与人性的贪婪、残暴和侵略性有关。战争的本质,是对社会生产力及人类社会、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,也是对人这个特殊、脆弱的生命体的最大伤害。伴随人类成长不断进行的战争,是人类最该警惕、最该反省、最该讨伐的“旷世魔鬼”。战争是有罪的。战争中的人,同样有罪。但人类渴望的和平,却又不会轻易到来,更是祈求不来的。有时,人类为了和平,还不得不拿起武器,参与战争,甚至陷入战争的泥沼,循环往复,难以自拔。人类用来战争的时间,远比人类安享和平的时间更长、更久。这未免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残酷悖论,一种巨大悲哀,甚至是人类用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终极困境。人类在和平的路上走得太艰难,太悲惨了。但人类最终还得擦干身上的血迹,继续往前走。前方是否会有曙光出现,在世界格局异常复杂、核武战争阴云密布的当下,仍是一个十分让人忧心的问题。
经过这番穿透性的探究与思考,我终于发现了“太平花”下面掩藏着的那些“深刻蕴涵”与“广阔世界”。但反观太平花原有的故事,我又发现:它无法承载如此庞大的主题。写小说的人都有个经验:故事必须与主题匹配。不然,孱弱的故事就会被沉重的主题压垮,根本站不起来、立不起来,小说自然难以成功。
三
后来,我签约阿来工作室,对四川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进行搜集、整理和影视转化。阅读了近千万字的文史资料和大量当事人的回忆文章,我突然发现,1934年冬天的成都,竟牵动整个中国的神经,处境非常离奇、非常微妙。彼时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,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,不得不战略转移,经过湘江血战,已到达湘西地界。当时中共中央有个考虑:将部队拉进四川,与川北红军在广袤富庶的川西地区汇合,建立新的根据地,并通过秘密渠道,指示四川地下党予以配合。成都进入红军视线。与此同时,南京的国民党中央,也开始关注四川、关注成都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蒋介石即令身边的军事专家分析、研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未来动向,得到的结论是:日本军队迟早会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。战争一旦爆发,日军会迅速集结力量,对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发起进攻。南京因无地险屏障,将很快失守。这时,国民政府要做的头等大事,就是尽快迁都。迁往哪里?军事专家们给出三个建议:一是陕西的西安,二是四川的重庆,三是云南的昆明。蒋介石则倾向于重庆。但盘踞在四川的地方军阀,却对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猜忌颇深,他们虽在1926年北伐期间就将手下军队归入国民革命军序列,却又极力阻止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四川,以便建立自己的“独立王国”,确保手中的权利不被削弱、损害。蒋介石只得想法通过各种途径,予以渗透。1934年冬天,国民政府专门派出一个地质考察大队来到四川,表面上调查地质、矿产等资源,实则为今后迁都四川搜集资料,作规划准备。而这时,日本陆军部及外务省,已通过潜伏在南京、上海等地的情报网,探知到国民政府的迁都计划,也派出间谍,潜入四川,搜集城市、道路、河流、桥梁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情报,以便在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后,对抗战大后方实施精准打击。于是,两国四方势力,即在偏居西南腹地的成都,展开一系列的紧张博弈。后来,中日战争全面爆发,四川地下党接到延安指示,联络军政学商各界,建立抗日统一战线,促成四川军队出川抗战。八年抗战期间,四川共出兵350多万,伤亡64万。此间,日军还不断派出飞机,连续数年,对重庆、成都、乐山等地进行无差别轰炸,造成大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,其中最为惨烈的,便是重庆“大隧道惨案”,一次就窒息、死亡居民近万。战争的残酷和本质,暴露无遗,和平的艰难与迫切,同样显现。这无疑是反思战争、书写和平的最佳历史事件,是完全承载得起我要表达的主题的。
四
《太平花》是我在地方性题材写作中的一次掘进,也是一次探索。我的体会主要有两点:一、当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性题材时,千万不要急于动笔,照搬故事,敷衍成篇,一定要把这个题材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场域去观察、思考,努力突破题材自身的局限,努力发掘它背后的复杂性、深刻性,并尽量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关联。有个作家朋友说:小说写作要有母体意识。我很赞成这个观点。上个世纪,文学界曾经长期流传着一个说法: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。我也同意这个说法,但我认为,要将“民族的”变成“世界的”,必须经过一个提炼、升华与超越的过程,即在独特的民族性中,发现更多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东西。如此,“越是民族的”,才可能“越是世界的”,否则,就会陷入为民族而民族的狭隘里。地方性题材的写作,也同样如此。二、虽是地方性题材的写作,但在艺术形式上,也要尽力考量、多作追求,比如结构上的安排,要打破陈规,要有新意;叙述语言的把定和整个小说的腔调,要与题材贴合,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;还有人物关系的设计、人物形象的刻画、故事的铺排与转承,都要精心考虑、细致书写。只有这样,地方性题材的写作,才有可能成功。
(黎民泰)





